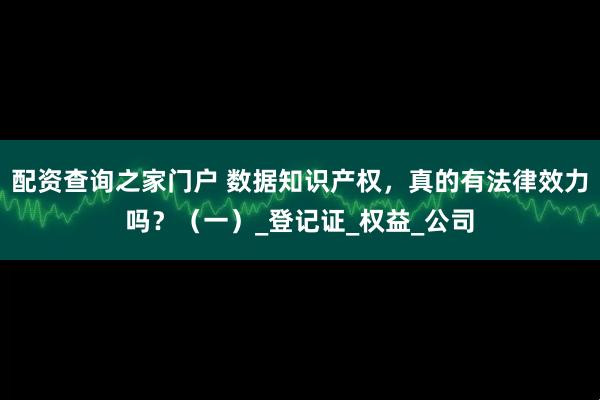《易》曰:鸣鹤在阴配资查询之家门户,其子和之;我有好爵,吾与尔靡之。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,关注、评论,为学、交友!
在清洗龙武功臣的前后,对中枢又作了调整,萧嵩替代了源乾曜,宇文融、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、杜暹。
1、庸相的仕途
萧嵩长着好胡髯,潇洒,威风,庄重,给人以信任感。

伟岸的相貌加上好胡髯,给他在仕途上安置了加速器,年纪轻轻就当了中书舍人。这个制作最高文件的美差,萧嵩无福消受,因为他不是个文才,在一次御前应急改诏文时出尽了洋相。玄宗命他将“国之瑰宝”换个同义词,他汗流满面,考虑了半天。玄宗以为他在精思密构,必出奇文佳句,把诏文拿去一看,竟只改为“国之珍宝”,一怒之下将诏文掷于地上,大骂他徒有虚表。姚崇不以为然,他坚信萧嵩前程远大。这个名相注重务实,他的看法自有道理。
吐蕃进犯,大将王君㚟(音绰)殉职,河西形势危急!萧嵩临危受命,出任河西节度使,对内不拘一格起用干才,修筑城墙,安抚百姓;对外反间计、攻坚战、阵地战多管齐下。吐蕃被打退,河西转危为安,萧嵩英名四扬。
谁说萧嵩无才?往日的轻视者闭口无言,姚崇的预言得到验实,玄宗转而刮目相看。
一道宰相任命书飞往河西军营,英雄凯旋而归,万众争睹风采。
新宰相到职后,今非昔比,身价百倍。玄宗把女儿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萧衡,每当驸马爷的母亲贺氏入宫朝见时,玄宗亲切地呼为“亲家母”。
天子和宰相联姻,皇家千金配相府公子,此等婚姻世间谁能得比?两个亲家翁聚在一起,谈国事,拉家常,家常中有国事国事中有家常。谈的次数一多,玄宗发现萧嵩没有什么过人之处,没有独到的见解,甚至和以前的萧嵩没有什么两样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,玄宗有些糊涂。
萧嵩是个人才、但只是将才、方面之才,而非相才、统筹全面之才。才非所用,良将变成了庸相。
君主不能轻易认错,玄宗也不想认错,他将错就错,要让萧嵩把宰相顺顺当当地做下去,渐渐地,玄宗觉得萧嵩的短处正是他的长处,缺少见解,人显得随和,不激进则处世稳当,这样的宰相在无用处中正有大用处。
庸相自有庸相的用处,萧嵩生逢其时,生逢其君。

玄宗在作了通盘考虑后,对萧嵩这个庸相进行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处理,让他变得大有用处。利用他在河西的声誉,遥领河西节度使,以威慑吐蕃,稳定西南局势。利用他在军界的威望及职业偏好,使开边政策得到有力的贯彻。利用他不善揽权的性格,有助于皇权的加强。利用他无力驾驭中枢的弱点,分权给宇文融,发展营利事务。利用他的亲家关系,使他产生出君、国、家一体的现实观念,将宰相变为君主的附庸。
于是,萧嵩成为玄宗名为举贤任能,实为使蠢用庸的招牌。
萧嵩高据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位置,心照不宣,两下方便,君臣各有所得。
萧嵩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,前任们的下场不由人不刻骨铭心,他清楚亲家不过是一层好看而不牢靠的纱幕,一不得法,这层纱幕并不比一块破布强多少。
萧嵩的官僚生涯是成功的,他少建树,少说话,做事斟的再三,不露破绽,使政敌们找不到攻讦的借口,加上玄宗的亲睐,他四平八稳,无难无灾。
2、“百日相位”宇文融
在庸相为首的中枢,不想当庸相的宇文融,也沦为了庸相。

他是个世家子弟,但他的发迹,不是靠家族的荫庇,而是凭自己的能力,在担任地方低级官员时,就受到了源乾曜的赏识。
他善于观察,在观察中发现男耕女织的国度,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口与土地,这是国家命脉之所在。
在地方上因人微言轻,一切无从谈起,当以监察御史进入中央政府后,他对从事司法、风化的本职只是敷衍了事,而把精力放到了对人口与土地的调查与研究上。他看到相当数量的人口脱离本籍,流浪在城镇,以逃避徭役赋税,他们的土地则被豪强大户所兼并,由此严重地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。
他利用本职向君主奏事的便利,上了一本,请对天下户籍和田籍进行全面整顿,让流亡人口返归土地,把无主荒地及被兼并的土地重新纳入政府控制之下。
有识之士、忠臣,玄宗对宇文融得出了印象。他决定,建议要用,提建议之人也要用,于是监察御史变成了覆田劝农使、租地安辑户口使。
检户括田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,在字文融和多名高级助手的督促下,成绩斐然,检户得80万户,括田得80万亩。到年终,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几百万缗。取之于民,还之于民,玄宗把这项收入全部用作各地常平仓的基金,以增强地方经济实力。
有人指责宇文融敛钱是为玄宗私用,此话不当。但地方官员为邀功而虚报户口数,则为实情。
宇文融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,而是借经济敲开政治大门。这一步他走成功了,不仅升为御史中丞,而且成了与玄宗直线联系的特殊权力人物。地方政府向上奏事,都先经过劝农使,然后再转给宰相。中央各大机构裁断事务,也要揣摩他的意思再定。他到地方巡视,总要召集百姓宣扬浩荡皇恩,百姓为之感动涕泣,把他称为父母。
政治明星,权势炙手,宇文融应玄宗需要而迅速崛起。朝廷上一片赞誉,说他于国于民有功。唯谏官杨相如、户部侍郎杨玚大唱反调,认为清查户籍田籍弊病不少,损害了社会的稳定。结果,不识时务的两杨被贬职外放。
对宇文融最为敌视的是宰相张说。他虽然清楚玄宗利用政治明星来分割相权的意图,但仍无法抑止对政敌的仇恨,尽一切可能地予以打击。灵活的宇文融不作正面交锋,避实就虚,最后抓住把柄反而把张说送进了大狱。
内心极为器重宇文融的玄宗,为避免舆论非议他纵容偏官倾覆宰相,装出怒容,以私结朋党的罪名把宇文融贬为刺史。一年之后,当大家认为张说、宇文融两败俱伤已成定局,并逐渐淡忘时,玄宗一道诏文,把宇文融直接调进了中枢,期望他创造出更大的财政效益。

宇文融的就职誓言,豪迈雄壮,激动人心:“我只需执政数月,天下必然安定!”
但实际上宇文融相绩平平,上任后除了提拔几个尚有人望的官员外,竟一事无成。无户可检,无田可括,也就无利可图,这使玄宗很快就对他失望。宇文融一变以前勤奋的风格,整天和宾客酣饮,以打发时光。遇到玄宗诘问,他对答如流,总有道理,弄得君主很不是滋味。在同政敌信安王李祎的争斗中,玄宗抛弃了宇文融,使他降为刺史,从而结束了区区百日之相的生涯。
就职誓言只讲准了一半,“执政数月”应验了为相百日,“天下安宁”却成了妄语。刺史也未做安稳,巨额贪赃案使他死于流放途中。
3、“官二代”裴光庭
强调一切按规矩办,照秩序行进的裴光庭,是一个地道的庸相。如果说萧嵩是才不当用的庸,宇文融是无可奈何的庸,那么,他是从传统中透出来的庸。
裴光庭和他的父亲相去实在太远。生活于太宗、高宗时代的裴行俭,是难得的文武全才。他懂兵法,懂天文地理,军功赫赫,是将士归心的一代儒将。他主持过掌握官员升降任免的吏部,以知人著称。在“初唐四杰”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大出风头之时,他断言,除杨炯较为沉厚可当县令外,其他三人因浮躁均不得善终。
事实证明了他的眼光。相反,许多不为人注意的文官武将,在他的提拔下,都成了名臣和名将。宛如先知先觉,不由人不佩服。
裴光庭是个孤儿,和寡母库狄氏相依为命。库狄氏以妇德被召为女官,裴光庭长成后凭此关系做了武三思的快婿。母子俩的政治倾向,若被曾反对高宗娶纳武则天的裴行俭亡灵所知,当不知作何感想?
幼年丧父的凄凉,武氏覆灭的牵连,使裴光庭养成了少言寡语的内向性格,他不善交际,没有知心朋友,在喧嚷纷闹的官场中独自默默无闻地生存着。

玄宗启用了他。裴光庭感恩戴德,工作踏实尽职。当玄宗准备到泰山封禅祭拜上天,为边境可能趁政治中心移动之际发动军事攻势而烦恼时,裴光庭提了个十全之策,邀请各国首脑、使节一同前往,以外交活动代替军事防御。
封禅队伍热闹气派,且省下了巨额军事开销。玄宗站在泰山顶上笑了,笑得舒意,笑出了上国君主的风度。于是,裴光庭进入了中枢,又从副手变为和萧嵩并驾齐驱的正宰相。
根据唐朝宰相常担任修史主编的惯例,裴光庭负责组织人员撰写从战国到隋的通史,为继承孔子著《春秋》的道统,定名为《续春秋经传》,拟定由玄宗修经,他和其他学者作传。因与时代风尚格格不入,这本他想藉以青史留名的著作始终未曾问世,成为史坛的一个话柄。
裴光庭明智地认为,水平不及父亲,地位却超过父亲,这应感谢命运,既然接受了好运,对恶运也当坦然处之。
当钦天监说出现不利大臣的天象,请做仪式进行消弥时,他不以为然地说:“若祸可用仪式解去,那福岂非用祈祷可求来?”
鉴于裴行俭慧眼识人的缘故,玄宗认为儿子必得父亲衣钵,把吏部交给裴光庭主持。
自唐初以来,选拔官员的标准主要是才能,资历很少考虑,形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。那些才疏学浅的官员,即使两鬓生霜,也难以升迁。然选官以才,全在于主官的鉴断,没有一定的模式。时日一久,钻营之徒买通主官,纷纷求得美职,以至弊端百出。
裴光庭决心做出些政绩来报答君主的厚望,他的改革方案名为“循资格”,即不论才干,论资排辈,按时升级。但消除了提升不公的弊端,又造成了压制人才的弊端,所以庸官蠢吏喜不自胜,高士英才愤慨怨恨。
宋璟的反对和萧嵩的异议,都未能阻止“循资格”的推行。裴光庭并不认为他们无理,但他认准另一个理:承平时期用人也应四平八稳,现存秩序才可得到维护。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庸相做庸,事,但玄宗不这样看,他迅速批准了这个方案。

为了权力,萧、裴两人争得不可开交,直到裴光庭的病逝结束了这场纷争。
4、耿直的宰相
新宰相人选的提名,极富戏剧性。
萧嵩推荐的是王丘,王丘却让贤转荐了韩休。萧嵩以为韩休性格平和,容易控制,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转荐,把韩休的德行在玄宗前大力宣扬了一番。谁知共事后,二人竟反目成仇,导致一起下台。
萧嵩看差了人,他根本就不了解韩休。
在拜相以前,他曾露过一次锋芒。当时他担任虢州(今河南省西部)刺史,因地处于洛阳与长安之间,君主车驾的来往,加重了本州的税收,他向中央提出本州不堪负担,应和其它州均平税收。宰相张说驳斥说:“若独免虢州,税当由它州承担,此是刺史欲立私惠。”饱识宦海险象的老吏劝韩休不要固执,以免得罪宰相。韩休义无反顾地说:“当刺史而不能救百姓之弊,如何施政?若因此得罪上面,心甘情愿。”
在他坚持不懈的请奏下,张说终于让了步。
韩休心目中唯有国家与民众,他把官场上所热衷的私人情面看得相当淡,也不大懂。什么知恩图报,什么忘恩负义,概不理会,任人说去。职位是谁给他的,这无所谓,要紧的是尽职。由此弄得萧嵩心中不快,玄宗跟着紧张。
低级官员李美玉犯小罪被钦定流放,奉旨主办此事的韩休向君主提出异议:“李美玉未犯大罪,只因位卑被判重刑,今朝廷上有大奸而不除去,是舍大取小。大将军程伯献依恃恩宠,贪赃冒功,侈糜铺张,臣认为应先除程伯献,再问罪李美玉。”
玄宗神情冷淡,拒之不理。韩休进一步说:“陛下若不驱逐程伯献,臣实在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!”
玄宗被震动了,新相的忠直、大胆,迫使他让了步。
这件事不过是个开头,韩休的耿直风格日见显露,他成了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的诤臣,不但公事要谏,连玄宗的私事也要谏,而且是以公的名义谏。谏得玄宗不敢放纵,谏得玄宗只好规规矩矩当个有道明君。

在以前不怎么出名的韩休面前,玄宗似乎变了个人,威严的风采减弱了,高度的自尊心消逝了,每当宴乐和游猎等事稍微频繁一些,总要担心地问左右韩休是否知道。然而用不了多时,韩休的谏疏必接踵而至。
君主当得苦,当得不自在,连享乐一下也要受到干涉,玄宗有些郁郁不乐。但他想起君主的责任,想起国家因此受益时,又觉得韩休是不可多得的好宰相。
有一次,他对着镜子想心事,左右侍从献媚地说:“韩休为相,陛下日见消瘦,何不将他逐去!”玄宗长叹说:“我貌虽瘦,天下必肥。萧嵩常顺从,他退后,我寝难安。韩休常力争,他退后,我寝可安。我用韩休,是为社稷,不是为自身。”
一半真话,一半假话,玄宗把冠冕堂皇的公道话说出了嘴外,把对韩休的不满藏在了肚里。
韩休对君主尚且是如此,对推荐他的大恩人更是一身的凛然正气。他极看不惯萧嵩没有原则,对君主一味逢迎的做法,每每在御前直抒己见,驳斥对方的不是,使得萧嵩下不了台,大失面子。
韩休不是书生,却有股书生气。宋璟对这股书生气大加赞扬,称作是“仁者之勇”,“仁者之勇”天下所闻,天下共赞。
萧嵩见韩休声誉鹊起,自己已难在中枢立足,遗憾且委曲地请求玄宗批准他告老回乡。玄宗不明底细地问道:“朕未厌卿,卿为何突然离去?”

亲家翁涕泪俱下地说:“幸陛下尚未厌臣,臣得以从容告辞。若陛下已厌臣,臣首级都难保,岂能再安然离去。”玄宗听出了弦外之音,他考虑再三,既不挽留无能的萧嵩,也不继续使用锋芒太盛的韩休,一纸诏文,萧嵩、韩休一起离职。
(正文完)
华林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